- 相关推荐
阅读趣事散文
说不清为什么,小时候就是一副书呆子相。只要是有字儿的纸,无论大小、无论在哪儿,都要去瞅一瞅,却对别的同龄孩子都爱玩的东西不走心,渐渐的也就离了群儿,显得孤僻起来。许多长辈和邻居问妈妈:“你家这小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也爱读书的妈妈,总是微微一笑,用一句“小孩儿自己爱玩啥玩啥”做了搪塞。在妈妈的纵容下,童年时的我为了看书可是出了不少洋相。如今,年近半百的我,回忆起那些趣事儿,还会窃窃地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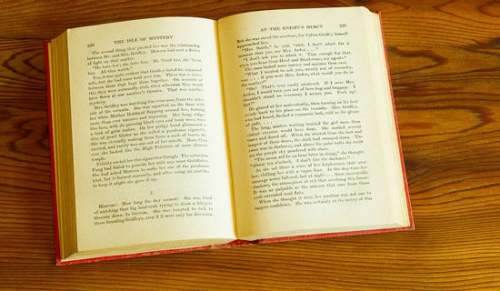
(一)糊墙的旧报纸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辽南农村和其它地方一样,物资匮乏,温饱难继,自然也就没闲钱儿买书看了,就连找到书都是很困难的。那几年,我如同一只饥饿的狼四处搜寻可看的东西。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把目光落到了每家的墙上。那时候的农家过大年之前,都要扫扫屋子,买些旧报纸把土墙裱糊一下。一开始愿意帮妈妈打下手,是要偷偷吃一口粘稠的面粉浆糊,成年累月吃玉米面的我是很难见到白面的。渐渐地,那即将糊上墙的报纸吸住了我的目光,只顾着看,忘了干活儿。更有甚者,忽然看见已经刷上浆糊的一面有条消息没看,就闹着看完再上墙,搞得老妈哭笑不得。后来,找到窍门了,旧报纸买回来,抓紧时间看一遍,再糊墙。自家的行,可以两面都看了,别人家就没办法了。只好等人家糊完墙,到人家屋里去看。全屯三十多家,够我看一个正月的。一开始,大伙儿都纳闷:这孩子怎么了,进了门打声招呼,就不再说话,两只眼睛就只盯着有报纸的墙瞅,看完这屋,去那屋。我妈后来跟我说,有的家大人跟她说,一开始还以为我看中他家啥东西,要找机会偷走。我问妈妈怎么回答人家的,我妈笑着说:“他只看中了你家糊墙的报纸。”
看的时间长了,我总结了几个步骤:先下后上,先近后远,不分新旧。先下自然是指糊在底下的旧报纸,大致是我一米多一点儿的个头平视及以下的部分。看这一部分的旧报纸只需站着或蹲着,自己可以自力更生。后上是指墙的顶端和房棚上的报纸,要看只能上炕或是踩凳子,这就要看人家脸色了。脸色好的,就爬上人家的炕或踩凳子去看,经常惹得爷爷奶奶和大娘婶子们大气不敢喘,怕我从凳子上摔下来。踩在凳子上看挺麻烦,看完一个区域,还得下来挪位置。另外,最难受的是仰着脖子,时间一长酸酸的。先近后远是指先看亲戚家和同学家的,后看屯里其他家的。姥姥舅舅大伯二伯家的自然是首选,完事儿就是同村几个要好的同学家,加到一起大概有二十多家,占去了全村的三分之二。去这些家看报纸心理比较放松,也比较自由,有时候还能在人家蹭点儿吃的;看另外十多家的糊墙报纸就得察言观色了,得趁人家心情好的时候去,还不能太放肆了,高处的一般只能靠我那双视力不错的眼睛尽力去瞅了,但大部分时候也只能看清楚副标题,内容是什么就成了心中痒痒的好奇梦想了。不分新旧这一条是指只要被糊上墙的报纸,亦或是书,一律纳入视野,绝不挑挑拣拣。现在想想,我自己都乐了:压根儿也没有新报纸 。
看糊墙报纸,心情有时迥然不同:最高兴的是这家上墙的报纸是本年度的,而且还是多地的报纸,要是能看到专登国际新闻的《参考消息》,那心情按现在的说法,可是爽歪歪了。反之,最不爽的,就是这家的报纸和我自己家的差不多 ,因为内容早已在老妈糊墙之前看过的。遇到这种情况,那就立即盘算马上把阵地转移到哪家的墙上。
几年下来,看多了旧报纸的我成了小伙伴中间最博学的时事宣传员。每逢下课时,周围总是围过来几个拥趸(现在叫粉丝),听我宣讲一下前段时间看报纸的收获,被崇拜的滋味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每每想起,还是拍拍一如既往酸痛的脖子,自我安慰一下,并留下两个字:值得!
(二)供销社里的卖书柜台前
那时候,有件事儿可是打破脑袋也要争着去的——跟大人去供销社。在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当年,距离村子四里地的供销社是三里五村购买生活日用品的唯一场所,跟着大人去,是有机会缠磨着弄几块糖或硬饼干解解馋的。去了几次后,对糖和硬饼干没了兴趣,倒是每次都赖在卖书的柜台前不走,直到从妈妈口袋里软磨硬泡出几分钱,买上一本薄薄的小人书才算作罢。惹得供销社里的人时不常的责怪我妈:“真惯孩子,学还没上,字儿也不认识,就给买书,他能看吗,净乱花钱。”妈妈的回答出乎意料:“我也想看看。”听到的人一脸的茫然,随即嘴角撇出一丝讥讽。买回来的书妈妈的确也看了,但她是和我一起看的,每一页都给我细细地讲了,那些个故事和画面至今我还记得:《海岛女民兵》、《东海小哨兵》、《小号手》、《闪闪的红星》,我也认识了一些简单的字。现在想起来,这供销社柜台里的小人书就是我的启蒙教材。上学认字多了以后,再进供销社,除了柜台里的“小人书”外,我的目光又盯上了柜台后边立着的书架,那上边摆着的都是被称作“大书”的小说,还有样板戏年画。样板戏年画我用看旧报纸的方式就搞定了。可那些“大书”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的,要想看只能想别的办法。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卖书的阿姨正是一个同班同学的妈妈。于是寻了一个机会,和那个同学一块儿去供销社,他去看妈,我去看书。混熟了之后,三天两头就去蹭一回书看。阿姨很温和,好说话,但书不能拿走,只能在柜台前站着看,还得防着一本正经的供销社主任。一本“大书”要去看好多回,经常是没看完就卖出去了,或是时间长了退货了。尽管这样,那段时间,在村供销社的柜台前,我还是囫囵吞枣地看完了《桐柏英雄》、《大刀记》、《艳阳天》等几部当时流行的小说。也许是自小养成了习惯,后来,到乡里中学上学,每天中午吃完带的玉米饼子,就往旁边的乡供销社跑,因为在二楼对着楼梯口处有一个比村子供销社卖书柜台宽出一倍多的售书区域。在六年的时光里,那里是我的中午天堂。每天中午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在那里享受视觉盛宴:假装要买,把书拿到手里看一会儿。开始的时候,自然要被营业员冷落白眼过。但时间长了有了交流,便也多了理解。《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俊友》等都是那个时期零打碎敲搞定的。也有很多次,将攒了许多时日凑够的钱递给营业员,换回来那本求人家特意留了很多时日的书,那高兴劲儿不亚于美餐了一顿只有在腊月杀年猪时才能吃到的萝卜片炖肉。尽管当时真实的状况是把午饭钱买了书,肚子在咕咕地叫。
(三)姥爷家的西屋
我家紧挨着姥爷家。于是,从记事开始,我就是自家和姥爷家来回儿跑着串,对姥爷家的屋子比自家摸得都熟,几乎哪儿都光顾过。但在1975年夏天的那个上午之前,姥爷家的西屋是个神秘所在,总是锁着。有时候,翘着脚扒着窗户看,影影绰绰的是放着些旧书,这可更激发了我的好奇,也暗暗在找机会进去看看。终于在那个夏天的一个上午,大人们都去生产队的地里锄草,无所事事的我无意间发现姥爷家的西屋窗户可以打开,这可乐坏了我,于是找了两块石头垫脚,爬了进去。看到屋里的东西,我差点儿乐晕过去:屋里的炕上摆着一摞摞整齐的杂志和十多年前的旧报纸,还有一些薄薄的小册子(后来知道那是党内学习资料),也看到了几本我从来没见过的书(也是后来才知晓是线装书)。见到书了,我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一本本看吧。于是,忘了时间,忘了饥饿。直到时至傍晚,妈妈慌慌张张地到姥姥家找我时,才发现了我。见到我在西屋,大家都屏着呼吸很紧张,怕姥爷不高兴。没想到姥爷见我脏兮兮的小脸儿,手里还拿着一本杂志,高兴地笑起来,记得还夸了我几句,同时叮嘱我,看完了别对外人说。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经过多半年的翻阅,存在西屋的书报杂志让我浏览了一遍。我也逐渐了解到了姥爷这些书报刊的来历:姥爷小时候上过不到两年私塾,略通文墨,在当年的农村,可是凤毛麟角。他还是土改时的农会干部,算是个基层老革命,长期在大队担任大队长和支部书记,西屋里的书报就是他二十多年来攒下的。因为有些资料是党内的学习文件,一些报纸还是文革以前的,流传出去不好。但姥爷也是个喜欢书的人,虽然是旧的东西,却总也舍不得丢掉,于是就码放整齐,集中收在西屋。姥爷没想到,这些书报刊滋养了外孙子贫瘠的心灵世界。尤其是培养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并伴随至今。如今,夜深人静之时,我站在书房的书架前,眼前仍不时出现姥爷家西屋的情景,还有姥爷得知我偷着进西屋看书时那开心的笑脸。
也许是宿命,喜欢书的我学了图书发行专业,上班去了书店。当我在书店的柜台里站定,看着眼前那些和我当年一样渴望的眼神时,我深知,这就是爱阅读人的那份真。岁月荏苒,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时代的发展,阅读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书也随处可寻,并有更方便的各类电子书陪伴人们,但浮躁奔波的人们却是减了阅读的兴趣,没了阅读的时间。在内心,我为他们遗憾,有时候也发几句感慨,家人说,天性不改,就是一副书呆子相。闻此,我也就释然了许多,心里流着一句话:人和人不一样。
【阅读趣事散文】相关文章:
初中散文阅读07-29
阅读周国平散文07-11
心事的散文阅读10-07
冬日散文阅读10-07
异地散文阅读10-07
秋思散文阅读10-07
念散文阅读10-07
初心散文阅读10-07
散文阅读:老屋10-07
散文阅读荒10-07